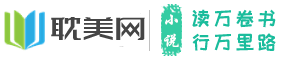109(2 / 2)
夏木繁抬头看向范阳平:“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,我要报警,这个人涉嫌谋财害命,他养的八哥就是人证。”
一旁的围观群众也都纷纷附和。
“对呀!就是这个人专门欺负外乡人。”
“他害死的那个人叫杨家维,尸体被埋在宾馆底下了。”
“八哥是他养的,不可能诬陷他。”
伴随着众人的话语之中,小八哥鸟呱噪的声音还在继续。
“外乡人有钱,弄死他们!”
“有了钱,盖大房子。”
“杨家维,杨家维埋在地底下。”
八哥鸟那粗粗哑哑的声音在大堂回响,仿佛有一把锉刀在张宏图的耳边反复不断的摩擦着。
张宏图那一颗经过岁月磨砺的心脏,终于扛不住内心巨大的压力。
他的嘴唇哆嗦着,整个人仿佛打摆子一样,却执着地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那个大大的叉。
范阳平走到张宏图面前,拿出锃亮的手铐铐住他双手,面色严肃地说:“张宏图,你涉嫌一起人口失踪案,请和我们一起到警局进行调查。”
夏木繁对范阳平说:“警察同志,这只八哥鸟就是证据,它是张宏图养了多年的鸟,它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和张宏图学的。”
旁边的人也开始鼓噪起来,帮着夏木繁说话:“对,我们可以证明,这只鸟就是张宏图养的,它说的话肯定是张宏图教的。谁知道张宏图背地里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,全被这只八哥听到、学到了。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,赶紧把他抓起来吧。”
范阳平与夏木繁交换了一个眼神,努力忍住笑,板着脸说:“张宏图,走吧。”
张宏图此刻被这只小八哥搅得六神无主,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。
忽然,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看向夏木繁。
夏木繁伸出一根手指比在唇边,做出噤声的动作。看到这个手势,八哥鸟立刻闭了嘴,变得安静无比。
张宏图内心一片冰凉,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眼前这个诡计多端的外乡人骗了。
被警察带回刑侦大队进行调查的张宏图,一路上不断的给自己心理建设。
——不要紧,现在只是这只小八哥说漏了嘴,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呈堂证供,只要自己不说出实情,谁也没办法逼他开口。
——退一万说,就算警察相信了小八哥所说的话,怀疑杨某某被埋在八方宾馆的底下,那又怎样?无凭无据的,难道警察敢推倒八层楼房子挖出尸骨来?
自己给自己打足了气之后,张宏图看向范阳平:“范警官,你们把我抓到警局去,总要通知家属吧?”
范阳平懒得看他,语气冷冷淡淡的:“哦,这会儿你家属应该也在警局里接受调查,没有精力来管你。”
张宏图一听有点急了,他是个妻管严,妻子就是他的主心骨,他大声嚷嚷了起来:“你们怎么把我妻子也带走了?你们为什么抓人?警察抓人不是也要有流程吗?我妻子和朋友一起吃饭逛街,难道这也犯法?”
范阳平哼了一声,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:“哦,聚众赌博,这个罪名也不小了。”
张宏图气得脸色都变了:“聚众赌博?开玩笑吧?她们几个没事做的娘们在一起打打小麻将,陶冶情操而已,怎么就上升到了聚众赌博的地步?”
范阳平耸了耸肩:“这我就不知道了,应该是有人举报吧。”
事情这么巧?同一时间点自己和妻子被带与不同的罪名被带到警局去,即使是再后知后觉,张宏图也知道大事不妙,内心开始犯嘀咕:是不是杨文静的报复开始了?简直是滥用职权!真是可恶。
另一边,孟莎和三个牌友在一家茶楼打麻将,突然之间警察冲了进来,将她们集体带走,麻将桌桌面、抽屉里的钱全部一缴而空。
和孟莎一起打牌的也都是拆迁户,有的是包租婆,有的在附近做点小生意。家里闲钱不少,孩子们也大了,平时时间多的很。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,喝喝茶、打打牌、聊聊天、逛逛街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突然之间警察将她们带走,搞得大家措手不及,都有点慌。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?这家茶楼的老板不是说了和警察有关系,不会有人有临时检查吗?”
“我们平时几个也就是小打小闹,输赢不过几百块,哪里就扣得上一个聚众赌博的帽子?”
“喂,赶紧打电话捞人,咱可不能留在看守所过夜,我听说那里连床都没有,上个厕所都要打报告。要是遇上运气不好,和那些杀人放火的恶婆娘关在一起,说不定还会被她们打一顿,好可怕的。”
几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,吵得孟莎脑壳疼。
和张宏图相比,孟莎警觉性更高。她很快就想起丈夫曾经跟他提过,杨文静临走之前放过狠话,要让他们好看,现在有此一劫,有可能就是杨文静派人干的,想到这里,孟莎的心反而安定下来。
大了不起就是被警察关几天罚点钱,反正她们的涉案金额也不大,只要自己不说出杨家维那桩案子的真相,警察也拿她没办法。
想到这里,孟莎安慰朋友们说:“没事儿,咱们也就是朋友之间打小打小闹打打麻将,不会有多大的事。等处罚结果出来和家里人打电话,让他们来交罚金就是了。”
同时被带到刑侦大队的张宏图和孟莎此刻高度默契,都打算不管警察说什么绝不瞎开口说话,免得被警察捉到小辫子。
杨家维失踪案已经过去十四年,在这十四年里张宏图、孟莎与警察打过无数次交道,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,两人早就已经娴熟无比。
只是两人此刻还不知道,与他们同时被抓的,还有一个锅炉工熊飞良。
审讯从熊飞良开始。
负责审讯的人,是顾少歧与孙羡兵、虞敬。
刑侦大队一楼的一号审讯室,青灰色水泥地面、金属材质的审讯桌椅,雪白的墙壁上写着大大的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八个仿宋黑色大字。
熊飞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环境,心中忐忑,脑袋低垂,一双小眼睛偷偷摸摸、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。
顾少歧的目光停留在熊飞良的左脸上,那里有一块很深的伤疤。
经过岁月的流逝,这一块伤疤已经愈合,新长出来的皮肉和原本的肌肤交杂在一起,让那一块的肌肉看上去有些扭曲。
顾少歧眯了眯眼,并没有说话。
可惜,如果当年有DNA检测技术,仅凭着那人体残余组织和精-液的DNA,就能够将凶手揪出来。
顾少歧审视着熊飞良脸上的伤,敏锐的从他脸上交错的肌肤中找到了几块明显的牙印。
为了看得更清楚些,顾少歧走近了几步,弯下腰来,眼睛与熊飞良的脸只有一尺的距离。
顾少歧穿着警察制服,外披一件法医的白大褂,面色严肃,他的突然靠近让熊飞良吓了一大跳,内心的恐惧令他身体下意识往后一仰,想要离顾少歧远一些。
熊飞良个子矮小、面容丑陋,平生最讨厌长得好看的男人,顾少歧就是他最憎恨、嫉妒的类型。他皱眉咧嘴,整张丑脸缩成了一团,声音里也透着惊慌:“你,你要干什么?”
虞敬和孙羡兵看他不老实,立刻站起,一左一右按住熊飞良的肩膀,大声呵斥:“不许动!”
审讯室里冰冷严肃的氛围,身穿制服的警察态度威严,这让熊飞良内心的恐惧感不断升级。
尤其是眼前这个身穿白大褂的警察死死盯住他脸上的伤疤,这让本就心虚的熊飞良越发紧张起来。
他嘶哑着嗓子大声叫了起来:“我就是一个烧锅炉的,你们不要欺负老实人。”
顾少岐的声音很冷:“老实人?我看未必吧。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?这么明显的牙印,到底是谁咬伤的?”
熊飞良的眼珠子乱转:“谁告诉你我脸上是咬伤的?这是我回老家的时候不小心摔伤的,当时流了好多血,贴了几天的纱布。”
顾少歧仔细查看他的伤口,眉头紧皱。
他转过身,拿起放置在桌面的模具。这是一个根据黄雁英的牙齿照片做出来的牙齿模具,红色的是牙龈,白色的是牙齿,看着并不美好。
顾少歧没做任何解释,拿起牙齿模具放在熊飞良的左脸旁边,开始进行仔细的比对。
熊飞良感觉莫名其妙,根本不知道顾少歧想做什么,但是却被他这动作弄得头皮发麻,好好的警察为什么拿出一个牙齿模型对准他的脸?
和夏木繁相处时间长了之后,顾少歧也学到了一些审讯手段。
不就是搞心态吗?这对医生来说像喝水一样简单。
有句话不是说了吗?天不怕、地不怕,就怕医生不说话。
熊飞良想要逃避,拼命地将脸往一旁躲,可是顾少歧并没有因为熊飞良的逃避而停止手上的动作,依然拿着牙齿印放在熊飞良的脸旁边。
顾少歧拿出游标卡尺进行测量,银灰色的金属卡尺看着像暗器一样,那冰冷的触感,令熊飞良吓得魂飞魄散:“喂喂喂,你要干什么?!”